窗外的梧桐叶簌簌落在阳台上,你望着茶几上冷掉的茶汤,第无数次听见钥匙转动门锁的声响。玄关处传来他惯常的咳嗽声,你下意识把蜷缩在沙发上的双腿放下来,这个动作像某种条件反射,仿佛在为即将上演的日常剧本整理戏服。衣料摩擦的窸窣声由远及近,在距离你三米处戛然而止——那是你们之间恒定的安全距离,如同五年来始终横亘在双人床中间的羽绒枕。
厨房里蒸腾的水汽在玻璃移门上凝结成珠,你望着他弯腰盛汤的背影,忽然想起昨夜他覆在你身上时急促的呼吸,那些带着药酒味的汗珠滴落在你锁骨上,像某种灼伤的印记。你数着壁纸上的鸢尾花纹,直到他发出困兽般的呜咽,这样的场景每月重复两次,精确得像设定好程序的机械钟摆。
晨起梳妆时发现鬓角新生了白发,你捏着那根银丝怔忡良久。梳妆台最底层抽屉里锁着泛黄的诗集,年轻时的笔迹在边角处洇开:”我要在你火红的吻中,焚尽所有枯萎的月光”。如今镜子里的眼睛却像深秋的池塘,连涟漪都泛着倦意。

上周同学聚会上,做心理咨询的老同桌握着你的手说:”人的心是会饿死的”。你笑着岔开话题,却在她怜惜的眼神中尝到喉头腥甜。深夜归家时看见阳台上晾着的男士衬衫在风中飘荡,突然想起母亲临终前攥着你的手腕说”婚姻就是熬鹰”,那时你嗤之以鼻,此刻却惊觉自己掌心早已布满相似的茧。
某个加班归来的雨夜,你在公司楼下遇见捧着保温桶的他。雨水顺着伞骨淌成珠帘,他发梢滴着水说怕你胃疼。你接过尚有微温的粥,突然发现他右耳后那道疤痕比记忆中淡了许多——那是你们初次争吵时你失手划伤的。他始终没去美容院处理,说留着才能记住当时的心痛。
梧桐叶落尽的某个清晨,你在晨光中凝视他熟睡的侧脸。那些经年累月的妥协与忍耐,不知何时已织成密实的茧,将两颗心裹成琥珀里的昆虫。你轻轻抚平他蹙起的眉峰,忽然明白婚姻原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,而是用半生时光在宣纸上晕染的山水——有人泼墨写意,有人工笔描摹,最煎熬的,是守着未干的画纸等岁月风干所有可能性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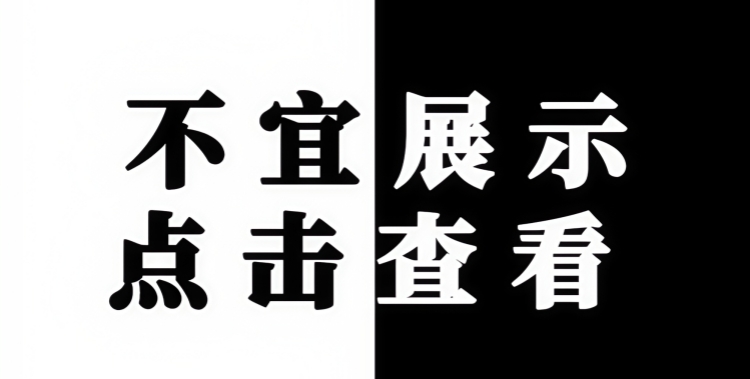

禁止留言联系方式
评论得积分,积分可在商城兑换奖品